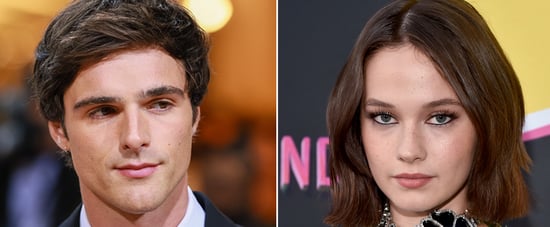臀位夹头出生的故事
我的宝贝在交付9年前去世了,我永远也不会得到

我们已近九年的儿子亨利出生后死于并发症臀位头截留。他是我们的第二个儿子,伤亡的一个家庭出生严重错误的。我们的助产士保证我们的孩子是头,当它发现他是臀位,她从不叫了救护车或服用药物进行在她包里停止收缩。亨利部分出生在4.5英里的桥,分开我们唯一区域医院产科病房。头被困在我是出生底部第一(医学专家所说的“臀位夹头”,这是一种常见的,几乎总是致命的臀位分娩期间发生),他几近窒息的我,中午我们坐在交通。抵达后在医院停车场,他从我的身体,我跪在越野车的后座。医生使用钳被称为直接从手术,我能感觉到他的手摇晃,他试了一次又一次免费的婴儿。亨利最终复苏的随叫随到的儿科医生但已经太久没有氧气。三天后我们将他从生命支持。
他头部被困在我出生底部第一,他几近窒息的我当我们坐在中午交通。
在他死后,我感到困在一个活生生的噩梦。我记得回家后去殡仪馆,彻底的沉默和感觉我们的房子空虚。空的空间,他的床被,精心挑选的栈尿布——它让我感觉我走在别人的生活,就像我永远不会再感到幸福或快乐。我记得去车库,他所有的婴儿被堆叠,哭这些货架抽泣,我翻了一番。我觉得我是彻底的和完整的底部的一个巨大的坑,我爬不出来。
老实说,这种感觉持续了好几年的增量变化。即使在我又怀孕了生下我的女儿,我死的强烈渴望和悲伤的儿子从未离开我。我觉得我没有他,我决定在家里出生,并最终决定杀死了我的孩子。带着悲伤的负担是一回事,但责任的负担是另一回事。我没有原谅自己,我不知道我是否会。
我听说80%的婚姻不去年整整一年之后,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压力是如此之大。我可以证明这些数字可能真相的,尽管我仍然嫁给了亨利的父亲通过我认为只不过是纯粹的意志力。我们参加了治疗几年亨利死后,和他的传球出现的主题,因为它总是。我记得辅导员,谁是一个老男人在他70年代,告诉我,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克服它。”At the time I said nothing, but inside I was seething. I remembered thinking, "I will NEVER get over Henry's death. I may move forward with my life, but I will NEVER, EVER get over it." The truth is that you just don't get over the death of a child. I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with you and that you carry forever. The intense grief from the early stages after your child dies thankfully doesn't last, but there's always a little part of you that stays attached to them. I never wanted to give that up, and didn't even think it was possible. Yes, you CAN find happiness again after your baby dies, but you don't get over it. A child dying is forever, as much as we wish it not to be true.
今年夏天将亨利去世九年周年。一开始,我们用来买气球,将信息附加到他们,在他生日那天送他们到天空。我们告诉孩子们气球会找到他们的兄弟,他会知道我们爱他。年后,仪式不再感到真实,我们发现最好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爱我们美丽的丢失的男孩在他的名字进行善意的行为。去年我们发放礼品卡,鲜花,和左画岩石为人们发现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称之为“亨利的一天。”I'll never "get over" Henry's death, but in many small ways, we've moved on and found beautiful ways to honor him. And though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have him back, that will have to be enough.